中國佛教的最初傳播:佛教音樂先被張騫所引進
古印度,是一個音樂非常發達的國家,因此,佛教音樂在古印度非常興盛。慧皎在《高僧傳》中記載大德鳩摩羅什的話說:“天竺國俗,甚重文制,其宮商體韻,以入弦為善。見佛之儀,以歌贊為貴。經中偈頌,皆其式也。”唐代的義淨和尚實地考察之後,也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中備述“西國禮教,盛傳讚嘆”的情況。中國現存的佛樂,與古印度的佛樂究竟是不是一回事?二者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呢?
提到印度佛教音樂傳入中國,人們便會想到慧皎那屢被引用的論述:“自大教東流,乃譯文者眾,而傳聲蓋寡。良由梵音重複,漢語單奇。若用梵音以詠漢語,則聲繁而偈迫,若用漢曲以詠梵文,則韻短而辭長。是故金言有譯,梵響無授。”看來,慧皎不但是佛教史家,他還深刻地懂得音樂。他正確地指出了佛教音樂隨佛教傳入中國後所遇到的難題。這個難題,是一切有辭之樂(聲樂曲)在進入另一個語言環境中都要遇到的難題,即譯詞配曲的問題。慧皎指出,假如用綿長、重複的“梵音”來配“單奇”的漢語,會出現一個漢字要配合許多音符而使曲調過於“繁複”的現象。而反之,假如用現成的“漢曲”來配合原來的梵文,則會出現因曲調過於簡短歌詞卻太長而容納不下的問題。但是,慧皎“金言有譯,梵響無授”的結論,卻未必是定論。因為音樂是分為“有辭之樂”聲樂和“無辭之樂”器樂兩種的,佛教音樂也不例外。無辭的“梵響”,無需去直接配合“金言”,因此也就不存在慧皎所說的問題。而有辭的佛曲,也並非沒有在中國的大地上歌唱過。
我們先考察一下無辭之樂的佛曲。說來令人難以置信,佛樂的傳入中土,竟要比中國人將佛教請入中國的時間還早!

最早把佛樂引進中國的人,是偉大的旅行家張騫。《晉書?樂志》中說,“張博望(張騫封博望侯)入西域,傳其法於西京,惟得摩訶兜勒一曲。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,以為武樂。”張騫鑿空,出使西域,共有兩次,第一次是從西漢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到元朔三年(公元前126年),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此時佛教尚未正始傳入中國。[1]當時漢政府的首席音樂家李延年根據這首“胡曲”所創作的“二十八解”武樂——中國漢代最早的軍樂——是什麼樣子,我們已不可能知道了,但張騫帶回的這首樂曲,卻似乎是一首佛樂。兜勒,應該是人名。吳支謙譯《義足經》中,有《兜勒梵志經》品,講兜勒如何從迷信外教而經釋迦牟尼點化皈依佛教的故事。“摩訶”在梵文中是“大”、“偉大”的意思,兜勒改變信仰,終於變成“摩訶兜勒”(偉大的兜勒),似是這首音樂的主題。這首佛曲大約可以被視為有史可依的傳入中國的第一首佛曲。[2]這首被漢武帝用作軍樂的“二十八解”佛曲,直到後漢時還用來給邊將揚威,“萬人將軍”方可使用。但魏晉以來,二十八解不復俱存,只能找到《黃鵠》等十曲了。而到了劉宋郭茂倩編《樂府詩集》時,已只能慨嘆“其辭俱亡”了。《樂府詩集》第21卷“橫吹曲辭”引“解題”說:“漢橫吹曲,二十八解,李延年造。魏晉以來,唯傳十曲:一曰《黃鵠》,二曰《隴頭》……”
看來,這首第一次傳入中國的佛曲在被當作軍樂使用後運氣不佳,興於斯、亡於斯,在戰亂中消失了。
再談有辭之樂。慧皎之所以斷言“金言有譯,梵響無授”,是為了推出另一位在中國佛教音樂史中不得不提的人物曹植。慧皎在概述了中國佛教徒對佛教音樂譯詞配曲問題的困惑之後,欣喜地寫道:“始有陳思王曹植,深愛音律,屬意經音,既通般遮之瑞響,又感漁山之神制,於是刪治《瑞應本起》,以為學者之宗。傳聲則三千有餘,在契則四十有二。”
曹植漁山制梵的故事,流傳甚廣,不但佛教的典籍多有記載,就連儒、道兩家,也對此津津樂道。南朝宋劉敬叔《異苑》載:“陳思王游山,忽聞空里誦經聲,清遠遒亮,解音則寫之,為神仙聲,道士效之,作步虛聲。”唐道世《法苑珠林》亦載:曹植“嘗游漁山,忽聞空中梵天之響,清雅哀婉,其聲動心,獨聽良久……,乃摹其音節,寫為梵唄……”此外,唐道宣《廣弘明集》等典籍中均載此說。
曹植(公元192-232年),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。自幼穎慧,10歲能誦詩文,他的“七步詩”和被其兄曹丕嫉逼的故事,在中國家喻戶曉。他不但才思敏捷,“少而好賦”、“所著繁多”,且通音律,“世間術藝,無不畢善”。他的思想亦很豐富,雖然從未皈依佛門,但作為一個悟性極高的知識分子,同時又作為一個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懷才不遇之士,他不可能不對當時最時髦的新思想——佛教本能地感到極大的興趣。他曾沉浸於佛典。《法苑珠林》稱他“每讀佛經,輒流連嗟玩,以為至道之終極也。”正因為他既迷戀佛教又有極高的文化教養和音樂才能,所以,他才具備“遂制轉贊七聲,升降曲折之響,世之諷育,鹹憲章焉”的資格。
中國古籍中談及作曲,常有“聞天樂”、“得神授”的說法,這或許出於古人對音樂創作的崇拜心理,也可能系古人為了追求一種神秘化效果而有意製造的氛圍。具體到這兩段記載,則包含著一種曹植所創佛曲與天竺佛教音樂有關聯的暗示。那么,曹植對中國佛教音樂的貢獻,到底是什麼呢?
問題的關鍵,在於如何理解“傳聲則三千有餘,在契則四十有二”這句話。
其實,“契”字,原為刻寫之意。契者,書契之契也,是含有“記錄下來,長久不變”的意思在內的。這樣,慧皎的話便很好理解了,就是“口傳的曲調有三千之多,其中被記錄下來的(很可能在慧皎時尚能見到的)有四十二首”。
本來“契”便是寫,把音樂寫下來,不是樂譜又是什麼呢?那么,曹植所用的樂譜,究竟是哪一種呢?我以為,很可能就是《漢書》中所講的“聲曲折”。王先謙(1842-1917年)《漢書》補註解釋“聲曲折即歌聲之譜,唐曰樂府,今曰板眼”。“聲曲折”以曲線狀聲音的高低婉轉,是一種較為原始的、直觀的,不甚精確的示意譜。它雖不能像現代樂譜那樣精確地限定音高音值,但卻能為使用它的人起到某種程度的“備忘錄”的作用。
“契”為樂譜,而且是“聲曲折”一類的曲線譜,這在現存宗教音樂典籍中是有實例可證的。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二七一二有《魚山聲明集》,二七一三有《魚山私鈔》,皆為旁註樂譜之經贊集,其譜既狀如“曲折”,兩集聲明又均名“魚山”,不但可以證明在日本僧人的心目中,佛樂譜系曹植所創,同時也可以作為“聲曲折”的實例,佐證《漢書》的記載。
有的學者不同意我的這種說法,認為我把“‘傳聲則三千有餘’理解為作曲三千餘首,謬矣!”認為“古往今來,亦少見有詞曲兼作三千首者,更少見一天寫三首,三年不斷,且首首傳世者”,因此,認為“聲”字,可作“音符”講,是“三千多個音符”當然,我並不認為將“三千有餘”的“聲”字解釋為曲調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釋,我也曾懷疑過這“三千”是“三十”之誤。但“古往今來”,“音符”卻從未作為一個音樂上的計量單位被使用過。換句話說,沒有一個音樂家會說,“我寫了多少多少個音符”。而且,僅僅認為曹植寫不出這么多音樂來不是充分的理由。恰恰相反,古往今來音樂史上卻不乏這樣令常人不敢相信的奇才。比如莫扎特,他一生中寫了22部歌劇,49部交響曲、40多首德國舞曲、26首弦樂四重奏、15首大彌撒、9首聖歌,130多首讚美詩……等等。拿出其中任何一部歌劇或交響曲來計算一下,其“音符”也不會少於“三千”。而實際上,這位作曲家只活了36歲。《三國志》本傳中稱曹植:“年十歲余,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,”有此奇才,唱出三千首曲調來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當然,這三千首曲調,曹植也許並不首首滿意,因此,才“在契則四十有二”。
那么,曹植就可以被視為中國佛曲有辭之樂唯一的創始人了嗎?恐怕也不能這樣說。因為在陳思王曹植之前,似已有讚唄的存在。從理論上說,既成僧伽,就要有禮佛之儀;既有禮佛之儀,則有讚唄之需。從東漢至三國,除曹植外,其他幾位早期的佛曲作家,基本上都是外族人。如支謙系月氏人,康僧會系康居人,屍黎密多羅系西域人,支曇龠亦系月氏人。他們所造梵唄,不可能沒有天竺、西域文化的痕跡。即使是曹植所創佛曲,也是在天竺佛曲的基礎上創造的。
這樣,似乎可以知道曹植的貢獻了:這位據說曾“七步成詩”的才子,也曾在三世紀初,運用,或創造了一種類似“聲曲折”的樂譜,“摹其音節”,記錄了大量他所聞的“天樂”——天竺的梵唄。他“撰文制音,傳為後式”,在中國佛教初肇的年代,傳播了來自天竺的佛教音樂,而“梵聲顯世,始於此焉”。
猜你喜歡:

如何評價左良玉?他為什麼要發兵南京?

“金陵十二釵”李紈是個什麼樣的人?李紈的最後結局?

五一勞動節的由來 五一勞動節的來歷及習俗是?

龍的崇拜之謎 世界上真的有龍嗎?

一個名出海外的中國士兵

正在消失山西寧武“懸空村”

紀曉嵐縱慾成性?紀曉嵐怎么死的?

歹竹出好筍:秦檜後人竟被乾隆欽點為狀元?

王世貞寫了那些著作?王世貞的個人影響

高漸離是誰 高漸離的生平簡介他是個怎樣的人

曹植是誰曹植簡介 歷史上曹植七步成詩是否確有其事

民國四大美男是誰?民國時期四大美男都有哪些

李淵和李世民是什麼關係?李淵的老婆是誰?

冒頓是在哪裡做過人質 冒頓是一個怎樣的人

慈禧一頓飯吃一百多道菜 但絕對不吃這兩樣東西

拿破崙死亡之謎:被侍衛毒死?
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國官兵

有人向你投手榴彈時應該怎么辦?

蒲松齡是一個什麼樣的人?他的妻子是誰?

漢高祖劉邦的第一個孫子:“齊哀王”劉襄

戊戌變法首領唐才常簡介 唐才常的結局

管仲茅草換黃金

解珍為什麼被逼上梁山?解珍憑什麼入天罡星之列?

鬼谷子的師父是誰 鬼谷子的徒弟是哪幾個他們都是誰

呂留良是誰?呂留良是怎么死的?

已滅絕的猛獁巨象或可復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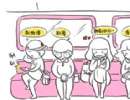
老玩手機會變醜?過度使用會讓你提前老化

忠達公圖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?圖海為什麼被革職?又為什麼被起復?

黑洞裡面是什麼物質?

巾幗烈女秋瑾是個什麼樣的人?秋瑾的詩詞